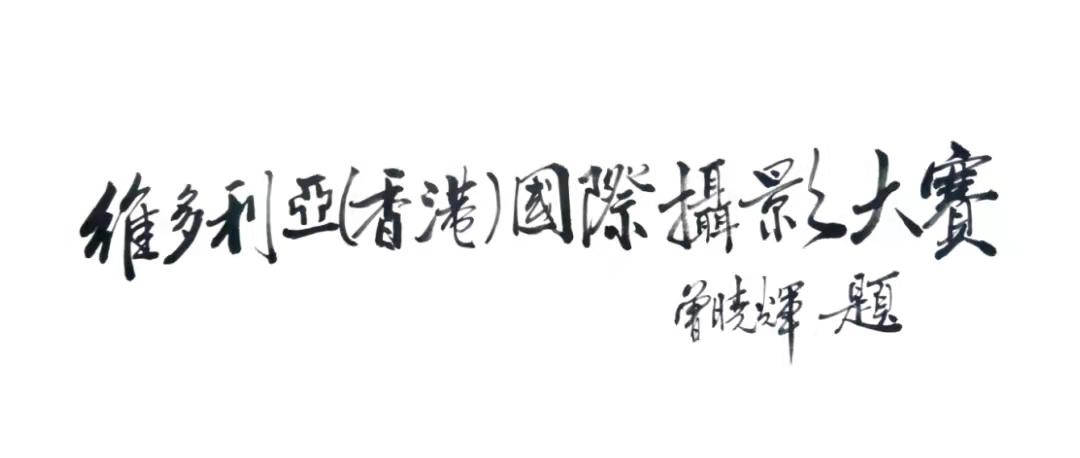从杨柳沙枣的树叶枯黄,到寒风砭骨,我已经好久没有回龙首山下的家了。
我说的家,是故乡。一直以来,我在这座人潮汹涌的省城里都没有归属感。喧闹的街道,五彩斑斓的霓虹灯,我感到的只有孤独。就如迷失方向的孩子。
疫情解封当天,我没有喜悦,可以说已经麻木。我是第二天裹紧衣服戴着口罩出去的。街上的路人都是戴着各种颜色的口罩行色匆匆,冷冰冰的眼神里只有茫然和惊惧。
我步行至黄河边。寒风里,河水依旧雄浑,浩浩荡荡。我竟然有种恍然隔世的感觉。逝者如斯,不休不止,而我困在钢筋水泥的牢笼三个月,却已心如死灰。
我孤独地沿着黄河岸步行,一直到前方一片荒芜。我看见野鸭不停地翻着水花,白鹭肆无忌惮地炫耀大长腿。我想它们是幸福的,因为这里就是它们的家。它们活得舒适安逸,或者说,活得踏实。
我在这座省城几十年,总觉得自己是羁旅在外的游子。世间所有壮丽的山山水水,都不如故乡的一草一木。再悦耳动听的曲调,都没有故乡的粗俗俚语听得亲切。
我给四弟打电话,问他现在能不能回去,他说问问村干部。我不抱什么希望,但心里还是有着期许。不要看村干部官小,执行领导的政策却是变本加厉,绝不马虎。
我回到小区,四弟打电话过来,说他已经问过了,本省的村民允许回来,问我是不是要回家?我说想回去看看,在外漂泊太久了。
晚上,我辗转反侧,抑制不住回家的激动,直到深夜才沉沉睡去。甫露曙光,我就迫不及待出发了。我没有走高速,而是选择车来车往的国道。
许是天色尚早,许是经济疲软的原因,往日熙熙攘攘的国道,现在仅有稀稀拉拉的半挂车风驰电掣。
我记得上次走这条312国道路,两边还是郁郁葱葱的玉米地,两旁摆满叫卖瓜果的地摊。现在却是满目疮痍,一片凄凉肃杀。
路上,我还不忘买两个烧饼。我不清楚是否真的饿了,因为每次想到烧饼两个字,我的肚子里都有咕噜噜的饥饿感。自小喜欢吃烧饼,从来没有厌烦过。
别人都喜欢挑三拣四,说哪家的味道好吃,哪家的不正宗。我从来不挑剔,我吃起来,只要是烧饼,都是同样的人间美味。
因为故乡是山川的川原,我自小就向往巍峨高山,山顶四季白雪皑皑,雄伟博大。现在悄然到了不惑之年,见惯各地的山水,却愈加怀念土地肥沃的故乡。
村里依旧冷清,座座耸立的楼房和干净的街道,掩饰不住破败的味道。在外漂泊的人太多了,不都是像我一样怀念故土。
有的人走出去时,估计就没有想过回来。有的人因为路途遥远,只能到年末才拖着疲惫之躯回来。
以前在外混得好的人,春节回来喜欢放烟花。炫耀一年生意兴隆,春风得意,这两年没有了。严禁烟花是一方面,关键是大环境下,每个人都活得很累。往日红红火火的生意,都很惨淡。
我记得村里的几个有本事的人,前些年顺风顺水,呼风唤雨。现在都很低调,还有两位过年也不回家,惧怕债主堵门。以前春节他们可是门庭如市,家里客主喧闹,目前已是门可罗雀,环堵萧然。
因为生计,每个人都挤破头拼命地涌向城市。现在随着经济大环境的恶劣,我想很多人都会回忆村里的人和事,无忧无虑吧!
回忆,是谁都刹不住的。每个人偶尔都可以回来一趟,但最终还是尽兴而来,败兴而去。
就如我,生活的省城距离故乡并不远,但注定已经回不来了。除了生计羁绊,至关紧要的还是现在的故乡,再已不是心里的故乡。
大街上,我碰到儿时玩伴立新。他比我小两岁,正裹着厚厚的睡衣步履蹒跚在地前面走。我没有和他打招呼,直接开车过去了。
立新小学毕业,我在读高中时,他就拉些水果四处叫卖。我在学校门口见过他,他见到我很高兴,非要给我一兜水果。我拒绝了,他弟兄多,家境贫寒,生活不易,何必去占这个便宜呢!
他结婚比较早,我高中没毕业,他就结婚了。他除了农忙时,都是开着面包车到县城卖水果。生活虽然艰难,但至少还能过得去。他是很乐观和知足的人,每次见面,他都是笑呵呵地打招呼。
五年前得他了偏瘫,现在是什么也干不成了。听说刚得病那会儿,他接受不了现实,自杀过一次。被家人及时发现了。他的父母哭着哀求他别做傻事。
我不和他打招呼,是因为我不知道和他见面说什么。或许视而不见也是一种仁慈。
家门口没人,我直接进了家。院子里面的草已经枯死,依旧受着寒风的折磨。堂屋是,已经盖了几十年了。四米五深,建筑面积接近三百平方。
我基本没有住过,以前的装修风格还有着时代特征,但墙面斑驳,油漆脱落。我到了书房,这是我独自的空间。
几千本书都堆积着,门窗紧闭,却沾满一层尘土。我擦去尘土,这都是我以前最忠诚的朋友,因为繁琐的生计,我抛弃他们多年。
这时,门外有人喊我,我听出是堂弟兄的声音,就匆忙出去。堂弟兄快五十了,胡子拉渣,精神委顿。两眼布满血丝。
堂弟兄说,我看见你的车在门口,想着你回来了,最近咋样?我笑着说道,还好,窝在家里三个月。
堂弟兄也笑了,我问村里还行吧?堂弟兄说道,肯定比市里自由,不影响吃喝,打牌。最糟心的就是不能出去挣钱。
我问堂弟兄,侄女的工作咋样了?堂弟兄叹口气,说再等等吧。我说好事多磨,不能把目光盯着咱市,其他地方有机会也行啊。
堂弟兄说,哪里都是一样,看她自己的努力和造化吧。我是没本事,已经尽力了。
我知道侄女师范毕业三年了,一直在私立学校教书。参加招教考试两次,都失败了。这种事,我也帮不上忙,就不谈这个话题了。
堂弟兄说,你今天不回去了吧,中午咱们喝点?我说不喝了,我回家看看,下午还要回去。你也少喝点酒吧,三个孩子都没安置呢!
堂弟兄说,我就这样了。能出去打工就打工,不能出去就喝酒打牌。闲着也是闲着。
堂弟对酒精有了依赖症。大冬天早上也要喝两瓶啤酒,白酒更是每天必喝。有人对我说过,你多劝劝国弟,他喝酒吓人,有几次喝多都小便失禁。我劝过国弟,他嘴上说心中有数,却依旧我行我素。
我没有去四弟家,四弟和侄子都在外面打工,干些苦力活。他们没有文化又能干什么呢?只有廉价的苦力了。
这两年形势不好,干活的时间还没有闲着的时间长。这是普遍而无奈的状况,前些年民工担心工钱讨要不回来,现在是工地活少,大部分都闲着。谁的生活如意呢?
我满打满算待了三个小时,就又匆匆忙忙折返了。我突然害怕见到更多的熟人,每个人都有辛酸的故事和捉肩见肘的难处。
庸俗的客套,难掩互相之间的不容易。刚出村口碰上学哥,他骑着电动车卖采回来。我们是兄弟,又是未出五服的堂兄弟。
他前些年打工时出了车祸,造成大腿粉碎性骨折。他在床上躺了大概有一年,现在还一走一瘸,有钢板在里面。干不成农活,就喜欢去打牌,打发时间。
他的儿子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去了武酒厂,女儿在读高中。诺大的压力,都压到嫂子身上。嫂子一年四季都在外地工厂打工。
简单聊了几句,我就离开了。学哥非要我把他买的馒头带走,说家里的考馒头片好吃,我说你留着吃吧。
回去的路上,我觉得很悲凉。进不去的城,回不去的故乡。这是我们这代人的痛和悲哀!
 会员投稿
会员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