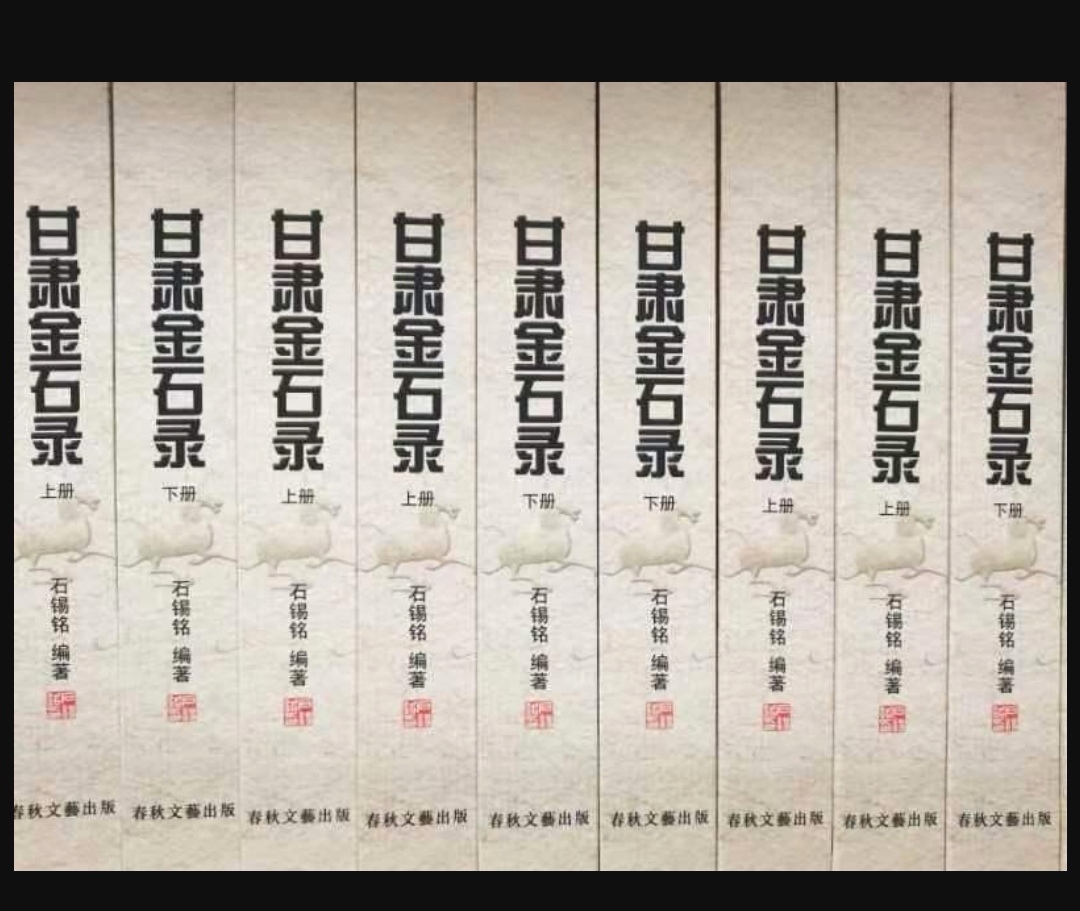
《甘肃金石录》自序:
从说谎的石碑说起
文/石锡铭
马王堆出土的《德道经》说:“死不忘者,寿也。”
于是,怎么不被人遗忘,就成了人生最大的事情;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只要不被忘,就是长寿。陇西锡铭想,金石从古至今的原始意义,就在于此吧。
也曾谦卑的向一些“科班的专家”请教金石的专业知识,居然听到这样的腔调:“金石不就是篆刻吗,那玩意儿我上学的时候经常玩,现在不玩了,没意思。”面对如此的“专家”,自然会思考中国式“开着宝马被人瞧不起”的根源。
最后发现,信仰的缺失和对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敬畏是当今穷得只剩下钱的一个当然理由。
奇特的甘肃文化现象
二十世纪前后,甘肃有两大发现,一是敦煌藏经洞,二是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但这两个文化现象是:地名留在了甘肃,“文化研究”都是“出口转内销”。
2014年冬,陇西锡铭在夏威夷与罗锦堂教授喝咖啡期间,聊起《甘肃金石录》收录敦煌金石资料的时候,罗老谈到民国政府对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事情。原来一直到大陆解放后,台湾的民国政府不要张大千这个敦煌文化的破坏者,直到五十年代末,张大千通过张群去给蒋介石说情,蒋介石的要求是张大千把敦煌剥掉的几十幅(具体数目忘了)必须无条件归还给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这件事让陇西锡铭意识到,张大千剥走的敦煌壁画数量非常庞大,甘肃仅仅留下了一个敦煌的地名及张大千临摹后刮剩的壁画。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真正意义上的敦煌文物,精品都在国外,最早的研究在国外,研究的集大成者不在甘肃;即“敦煌文化”是彻头彻尾的出口转内销式的文化。
1987年,秦人四大陵园中的第二、第三、第四陵园,即雍城陵园、芷阳陵园和临潼秦始皇陵园都在陕西省先后挖掘发现,并且文物得以保护。同样是在1987年开始,位于甘肃礼县的秦人第一陵园——西垂陵区,在本地农民、当地官员、一些大学教授、不法文物贩子的围剿中,用时十年,洗劫一空。据称,当时最多的一天这一带盗掘古墓的达数千人之多,有的带着铺盖卷,拿着锅碗瓢勺,当地就餐,晚上架起灯笼火把、架子车,形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有地方要员、知名学者积极参与的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挖墓风潮。地方政府的腐败,再次让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皇陵文化”出口转内销,即大量大堡子山秦皇陵文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倒卖出国,文物精品出口到了国外,研究又一次起源国外,集大成者不在甘肃。
陇西人新编的谚语:“某家父子升了,博物馆里空了。”这种官员明目张胆的监守自盗,然后全家鸡犬升天,而博物馆馆藏都是赝品充斥其中的奇特现象,是不是甘肃贫穷的根源?
甘肃的这种奇特文化现象值得深思。
2015年,媒体报道称“流失境外20余年的32件春秋时期秦国金饰片”回归后,“国家文物局研究决定,将其全部划拨甘肃省博物馆永久收藏和展示”。在没有人追问这些国宝是谁盗掘、盗卖出国,放任这些有组织的盗掘秦皇陵的罪人开着古玩城和古玩店的时候,我倒真心希望这些国宝继续保存在国外的博物馆,担心哪天我们在甘肃看到的又是一件件赝品,而珍品再次“流失”。
总之,陇西锡铭在1998年开始专心搜集甘肃诗词、编辑《全陇诗》、亦开始搜集甘肃金石资料的同时,也在关注、思考甘肃文化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奇特现象。
名流、石碑与谎言
经过整理金石资料,陇西锡铭发现,名流、石碑和谎言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初中时学过一篇课文《李愬雪夜袭蔡州》,讲的是唐朝一个靠奇袭、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读了唐末五代时罗隐的《说石烈士》,才知道韩愈的《平淮西碑》说谎之事。时任淮西节度使的吴元济再次背叛朝廷,唐宪宗命宰相裴度为元帅、李愬为大将率兵征讨吴元济。公元817年冬天,李愬亲率精兵五千人,乘雪夜急行军百余里突袭蔡州,攻入汝南城,活捉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战役结束后,唐宪宗就命韩愈撰文记述平淮西战役的胜利并刻碑。韩愈这位曾亲历淮西之战、被后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学家,撰写《平淮西碑》时把雪夜突袭蔡州活捉吴元济、平定淮西叛乱的功劳记在了宰相、平藩元帅裴度名下,把李愬受降的叛军将领称为叛将,引起了李愬部将的极大不满。李愬的妻子是唐安公主的女儿,她进入皇宫找到宪宗诉说韩愈的《平淮西碑文》于事实不符。同时,李愬的部将石忠孝看到碑文里没有提到李将军的名字和战绩,一怒之下,推断了石碑。唐宪宗下令把石忠孝抓进大牢。石忠孝在狱中,又用刑具打死了一名狱吏。结局是宪宗皇帝亲自审讯石忠孝,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为了平息事端,唐宪宗赦免了石忠孝,又命翰林院学士段文昌重写了《平淮西碑》文,但对学术造假的韩愈没有做任何处理。假设没有石忠孝这样不怕死、敢说真话的部下;假如李愬的妻子不是唐安公主的女儿,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就不是《李愬雪夜袭蔡州》,而肯定是《裴度雪夜袭蔡州》了,媚上的韩愈也就成功的利用手中操弄文字的权利篡改了这段历史。可笑的是,到了宋代,蔡州出了个知府陈向,他竟然命人磨去段文昌的碑文,又重新刻上韩愈写的碑文,所以苏轼调侃道∶“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两通《平淮西碑》的缘由。颠倒黑白的一通碑,因为是知名文痞写的而被人津津乐道;反映历史事实的一通碑,总有人想让它消失。这个不断演绎的事件,是不是从侧面说明,名流都喜欢撒谎?
从没有刻碑之前就随意篡改历史,到已经刻碑之后,一块块坚硬的碑石还有人不断的随意篡改,那我们现在读着的历史,有几件是真的,又有多少是谎言?这就不得不让人深刻思考,为何我们的国家一旦外族入侵,瞬间会出现大量的“汉奸”,难道和名流、史学家、文学家无节操的媚上、任意占据他人功劳、恣意篡改历史的恶习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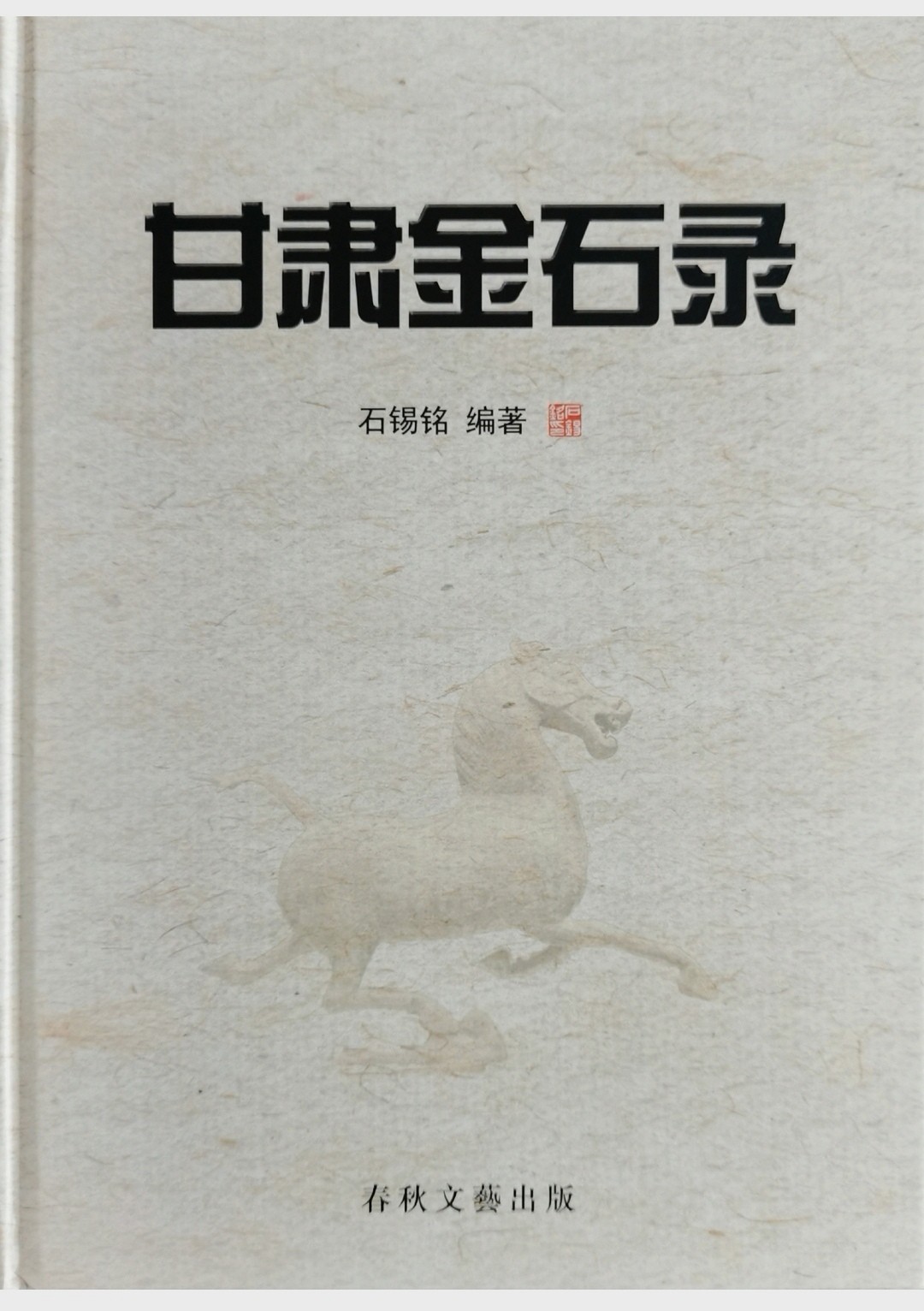
甘肃金石 丰富雄厚
甘肃金石以内容为纬,丰富雄厚,令人惊叹。简单分类如下:
1、弥补正史缺失,纠正正史谬错。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这句名言点出了“正史”之纰漏。如武威的《武禹亭碑记》载:“先是己卯洋匪蔡牵以四十二艘犯安平鹿耳门之北汕,总兵爱新泰闻乱,以水师副将游击等出巡洋,而陆管将并无可倚托者,乃委府君。……是时府君已两中箭伤,而犹力呼维光等守栅,事急下台立潮中,犹各拼死力,手刃贼首十余人,乃同遇害。洎雨息,贼纵火烧栅,火光烛城上,而总兵以下益慑伏不敢出,所谓救援终亦不至。……出北门里许得之北坛僧寺,僧吉畴昔夜有四五人,驾芦桥自载是以来,入佛殿。玢、瑷与继曾蒲伏入寺,望见果是府君,继曾于是手具汤为熏濯创痕,细书分记。曰:刃创十一也,项左偏三、颈右偏二、左手二、右胫骨二、腹左右各一。曰:箭创三也,胸一、左腰胁二;曰:长戟创三也,右足二、右胁一。书讫贴扎上,使玢、瑗黻黼衣缝。……又明日,总兵以下千余人来吊,玢、瑷哭受吊,爱新等善抚慰之,为眠治棺殓而去。事闻廷议,以情事不符,命厦门道朱公察情覆奏。……府君之死事安平,颠末如此,今距二十余年矣。时不孝瑶、琚、瓒还乡省墓,安平之役竟不获执,羁勒从侍绝缨血刃于仇虏之胸,以身分难,痛何如哉。”碑文详述了武威人武克勤在台湾安平之役阵亡的经过,尤其功被“侵占”,“颠末如此,今距二十余年”。
再如唐代柳宗元撰文记载徽县的《兴州江运记》,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历史地理文献。文载严砺“节用爱人,克安而生。老穷有养,幼乳以遂,不问不使,咸得其志。公命皻铸,库有利兵。公命屯田,师有余粮。”俨然是一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突出,品德高尚”的好公仆。但《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七列传第六十九严砺》:“严砺,……然轻躁多奸谋,以便佞自将。……砺在位,贪沓苟得,士民不胜其苦。”这说明严砺绝对是一个善于搜刮民财、祸害一方百姓的贪官。
此类弥补史料缺失、侧面印证个别正史虚伪性的金石资料,比比皆是,是金石文字中存量最多的一类资料。
2、武都柳林镇的《阶州太守田公刺虎记碑》可以知道,约900年前,陇南山高林密,老虎成群。因此,《阶州太守田世雄刺虎记》之类的金石资料是研究甘肃乃至西北生态演变的珍贵石刻档案。
水资源是甘肃现在及以后的主要问题,但不是近代才开始的。如武威高头坝与乌牛坝之间的争水纠纷,已成为河西水案的典型案例。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二日立《凉州卫高头坝与永昌卫乌牛坝之争水利碑》;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在高头坝上二泉处立小碑一座,镌刻“高头沟”字样,在乌牛坝下二泉处立小碑一座,镌刻“乌牛坝”字样,又在沙河口大堤上立《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用水执照水利碑》;雍正十二年十二月立《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用水执照水利碑》,乾隆九年十月,九月二十日在县衙前立《判发武威县高头坝与永昌县乌牛坝用水执照水利勒石碑》;乾隆十六年六月立《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用水执照水利碑》,民国三十八年《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水权案文》,说明历代对因水而起的纠纷的处理难度很大。从以上碑文中可知,仅在康熙年间,大的纠纷有11次;雍正年间,大的纠纷有3次;乾隆年间,大的纠纷3次。此外,如临泽的《违规筑坝争占水利碑》、《疏通水利碑》;武威的《泮池水利碑记》、《怀六坝磨湾泉源水利碑记》;古浪的《渠坝水利碑》、《长流川六坝水利碑记》等皆说明,水对甘肃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3、不同时期的文化、教育、宗教以及倡导勤俭、节约、务实的生活态度的碑刻铭文,今天仍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如时任凉州知府欧阳永裿撰写的《敦节俭条约碑》:“富者不足十之一二,而贫者即不下十之八九。揆厥所由,实因俗尚奢侈,不知节俭之所致。而其弊始自绅衿富户,夸多斗靡,奢泰滥觞,因而中产以下,亦不自量有无,随声附影,互相效尤。”“尤望绅衿士庶,有心善俗者,加力剔除,去奢就俭,则风俗人心,胥相维于淳厚矣。”“丧祭之费用,宜节也。”“嫁娶之费用,宜减也。”“酬酢之馔饮,宜简也。”这和今天国家提倡的勤俭节约一脉相承。
4、反映籍贯、族群、姓氏的渊源变迁的金石资料,为研究甘肃此类问题保存了珍贵资料。籍贯、族群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人为的“误会”,表现之一为同一家族的碑刻文字,随着时间推移,对同一祖先的籍贯记载迥异。如李唐王朝,著名于世,记载各异,有的“陇西成纪人”,有的“陇西狄道人”,有的“陇西人”。但都好像刻意隐瞒“陇西鲜卑人”的历史。
陇西汪家,显赫于元代,后代大多碑云“其先徽州府歙县人。始祖有曰华者,当隋之李,逮唐受禅,知天命有属,则奉籍以归,得封越国公。卒,进越王。子达袭爵,移镇陕西巩昌,遂家于盐川,即今漳县是也。历宋及金,相传为汪古族都总管。追元兴至公,八世祖世显以武功拜巩昌便宜都总帅。”现存的《总帅汪义武王世显神道碑》也是这么写的,但此文作者杨奂早期文集中收录的《总帅汪义武王世显神道碑》一文,就没有“系出南京徽州”句。显然,核心人物“汪世显”的碑文系后来人修改过的。与之可以佐证的如姚燧所作、载于《牧菴集》的《王鹗忠烈神道碑》以为“汪本姬姓,世掌汪骨族,因以为氏”之说;《汪忠臣神道碑》所载说:“公王姓,由大父彦忠世汪古族,故汪姓”。同一祖先的后代,说法各异,留下了很多研究的空间。
如西安碑林中保存着书法史上著名的《曹全碑》中,称曹全是“敦煌效谷人”,并追述曹氏先人自秦汉之际就“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说明敦煌之有汉族出身的曹姓人家,可以远溯到东汉时期,显然这支曹姓与谯郡不是一支。但以后这一支在敦煌的历史上都归附到谯郡名下,因为曹操尽管奸雄,但知名度总是比曹全高一点的。
5、改姓、赐姓是姓氏研究的一个范畴。《甘肃金石录》资料中搜录有唐朝的几个姓氏发展,如《唐武威郡人安暐即李国珍墓志》载“以忠勇见进,武艺知名,……稍沐洪恩,特赐嘉名,改氏皇姓。出生人死,实为士卒之先;执锐被坚,颇历日月之久。其改讳曰国珍”,安姓改为李姓。《唐陇西李氏独孤季膺墓志》载“润州司马独孤公……讳季膺,字季膺,本陇西李氏,隋文帝赐独孤氏。皇唐玄宗时复旧,代宗时又归所赐。”陇西李氏改为独孤氏,旋又改为李氏的一个反映。
浑水摸鱼式的篡改史书,让人换姓不改名,最著名的莫过于“老子”姓氏的改变。诸子百家中孔子姓孔、荀子姓荀、庄子姓庄,孟子姓孟,以此类推,“老子”应该姓“老”才对。我一直怀疑有人篡改过“老子”最早的记载,目的是硬让他姓“李”,成为所有李家人的祖先,李唐王朝,有这个能力。
6、甘肃经常地处边陲,战乱频繁,因此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创伤的碑刻非常多。如清同治年间的回乱给甘肃人民造成的伤害,《榆中例赠马老太翁暨太母张孺人之志表》载:“逆回所过尽成蔓草荒烟,举家之人忽如伯劳飞雁,由是十庄九空百不存一。”《永靖褒扬节母杨太孺人墓表》载:“在昔地方之变,河狄蠢动,风声鹤唳,日无宁晷。”《庆阳重修泰山庙正殿神像记碑》载:“同治七年三月,郡城失守,回匪猖獗,可怜一炬,尽成焦土。”《陇西李成蹊墓志铭》载:“同治五年八月……一女名金环,适儒门祁氏,城陷之日,劝夫现虞负子逃去,已独守翁柩,嫂挽不肯出,既贼至,自毁其面,伏柩哭,贼将逼之,乘间登小楼白杀。”《陇西傅巩亭军门功德碑》载:“狄河逆回袭陷郡城,……时城中烽火烛天,积尸与城齐,血流潺潺成沟渠,百姓初无生望。”真实再现了回匪“打、砸、烧、杀、抢”的凶残本质。奇怪的是,我们教科书学习的是回民起义,难道起义就是匪首白彦虎之流勾结外国势力,和“IS”一样,采用“屠村式”的滥杀无辜百姓?
7、通过建学宫、修寺庙等提倡良好社会风尚和反映风俗习惯的金石资料,存文最多。如敦煌莫高窟的不断扩展,是世族大户和商贾贵人出钱捐粮,请人开凿洞窟、供养佛像的过程。每建一窟,都要竖碑记事,颂扬功德,耸立于莫高窟第148窟的《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碑即属此类。今天寺院庙宇的发展,还是这种模式。
8、金石是传统文化的体现,也是传承的主要载体。如《沙州报恩寺故大德禅和尚金霞迁神志铭并序》中的时间称谓——“时辛巳岁龙集大荒骆四月廿八日”,大荒骆,又作“大荒落”、“大芒落”、“大芒骆”。太岁运行到地支“巳”的方位,这一年称大荒落。《尔雅·释天》:“(太岁)在巳曰大荒落。”《史记·天官书》:“大荒骆岁:岁阴在巳,星居戌。”因以为十二地支中“巳”的别称。《史记·历书》:“祝犂大芒落四年。”裴駰集解:“芒,一作‘荒’”张守节正义引姚察曰:“言万物皆炽盛而大出,霍然落之,故云荒落也。”《史记·历书》“彊梧大荒落四年”唐司马贞索隐:“强梧,丁也。大芒骆,巳也。”,这些古代时间、干支等称谓,五花八门,丰富极了。
9、特殊金石资料,弥足珍贵。如庆阳市正宁县宫河镇邓家川村玉皇庙的一块明正德年间石质地契,是一份难得的经济史资料。这可能是全国范围内难得一见的石质地契。此类文献,为研究世界文化的发展,补充了宝贵资源。
10、大唐帝国李家的后代,在墓志铭里追溯祖先,显得非常矛盾:有陇西人,有陇西狄道人,有陇西成纪人,有陇西姑臧人。为何如此矛盾?不论。为了便于编辑,大唐皇族统一于“陇西李唐皇室”名下。
11、甘肃人对文物的漠视,是思想贫穷的一种体现。如大到敦煌、礼县大堡子山文物的破坏,小到碑刻的不重视,比比皆是,不再赘述。
总之,通读《甘肃金石录》,能从各个层面,不同角度了解到甘肃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民生、医疗、官匪等社会现象、人文发展,等等。
甘肃文化 仍须努力
内容为纬,则岁月成经。
《甘肃金石录》所收录的崆峒山上的《太昊碑》,是甘肃有记载的最早的碑刻;甲骨文中“尞”字的7种不同写法彩陶及距今4500~4000年冶铸青铜器铭,此外《商卤》、《商彝》、《周彝》、《周鼎》、《周彝龙尊》、《周凤虎盉》、《周四大钟》等都证明,甘肃远古时代的文化非常发达,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华文明,逐黄河及其主要支流,自西向东、向南发展,而非传统的自中原向西北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甘肃出土的金石非常丰富,如《战国怪兽噬鹿铜牌饰》、《匈奴青铜鸟头》、《秦公敦》、《庄浪秦惠文王二十六年诅楚文石》、《永登青铜刀》、《礼县鹤袅形金饰片》《礼县亚父辛鼎》、《礼县秦公簋铭》、《天水家马鼎铭》。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现在秦自天水清水向陇南、陕西的发展历史,基本清楚。20世纪20年代,甘肃礼县盐关-罗家堡一带出土“秦公簋”;90年代初,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掘,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其中青铜重器百余件,多有“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铸用壶”、“秦公作宝簋”等铭文;最大的一座出土铜器9件,包括鼎3件、甗1件、盂1件、短剑1件等等。这些金石,是先秦帝国从甘肃发展,携剑入关统一华夏民族的有力佐证。
三国时期著名的“六出祁山”的事迹,早已为国人所称道;而祁山,就在甘肃礼县。
盛唐的建立者,因历史学家陈寅恪表述为“关陇集团”而成名。关即今天的陕西关中地区,陇指今甘肃乌鞘岭以东、宝鸡以西的甘肃广大区域。所有李氏宗亲的墓志铭,均署名“陇西人”。而唐代李白题写的《宝志公象赞诗碑》,因为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书写、唐朝画圣吴道子作画刻在石碑上被称为“三绝碑”;唐宰相裴度撰、书法家柳公权书写、名匠刻字的“三绝碑”《李晟墓碑》,也和甘肃人有关。
西夏碑,汉译为“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对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社会经济、土地制度、官制、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国名、帝后尊号、佛教盛况等极具价值。
通过这些宝贵的金石资料发现,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甘肃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大省。
许多年前,有人问陈忠实在忙什么?陈忠实回答说:“我在羞先!”原来《白鹿原》在入围“茅奖”时未能通过,理由是:其内容与体制冲突。于是陈忠实为了获奖,不得不按有关部门的意见将作品做了修改与删节,就像白灵“被混迹于革命营垒中的邪恶势力活埋了”。可惜甘肃,陈忠实这样的文人都没有。总之,不可回避的现实是,整个甘肃文化环境生态沙漠化,恢复希望渺茫。甘肃文化,仍须努力。
空谷绝响 千古幽幽
本书取名《甘肃金石录》,囊括陇西锡铭20年来积攒的甘肃金石资料的大部分内容。可以非常自信的说,这是甘肃乃至全国金石文化领域,靠个人的热情和执着完成的独一无二的文化大餐。
只是出于爱好,花费20年时间,编纂甘肃金石方面的鸿篇巨制,资料搜集、编辑、校对皆陇西锡铭一人勉力为之,终归力总不逮,错谬一定不少。在此先致歉意。
编辑过程中,遇到原稿陇西锡铭自认为有错误的,诸如汪楷之《陇西金石录》出现的“松楸日暮(误为墓)起悲风”、“秦郡三贤(误为闲)”、“编(误为偏)者”,《漳县金石录》中的“汪世(误为氏)显”等,一面录入,一面勘误。这类错误,每个原始资料中都有,如果没有辅助资料参考,此类错误,更多的陇西锡铭可能还是照抄了下来。
诸如《漳县金石录》之同一文、同一页就有“此碑现存甘肃武山县文化馆”及“现存漳县博物馆”的矛盾注解。此类问题,陇西锡铭能查到相佐证资料的,确定资料;如果类似的矛盾,查不到相关资料的,只能根据文章本身来取舍。
还有一些,一篇文章几本书都有收录,但各自关键的记载出入较大,陇西锡铭尽可能选择编辑好一点的册子作为校对的底本,别的仅仅参考。
诸如此类错误,积少成多,距“严谨”二字远矣。
总之,种种原因,本著的错误会非常之多,还望海涵、指正、赐教之余,希望后来有专业人士不吝批注、校对。
乞请名流、专家、教授、博士、学者人等,引用或者抄袭本书部分资料时,请注明出处,可乎?
呜呼,云中白鹤,正本追远;千载寂寥,此著谁鉴?
是为自序。

陇西锡铭
2016年11曰1日初稿
2017年12月20日修改于深圳
 会员投稿
会员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