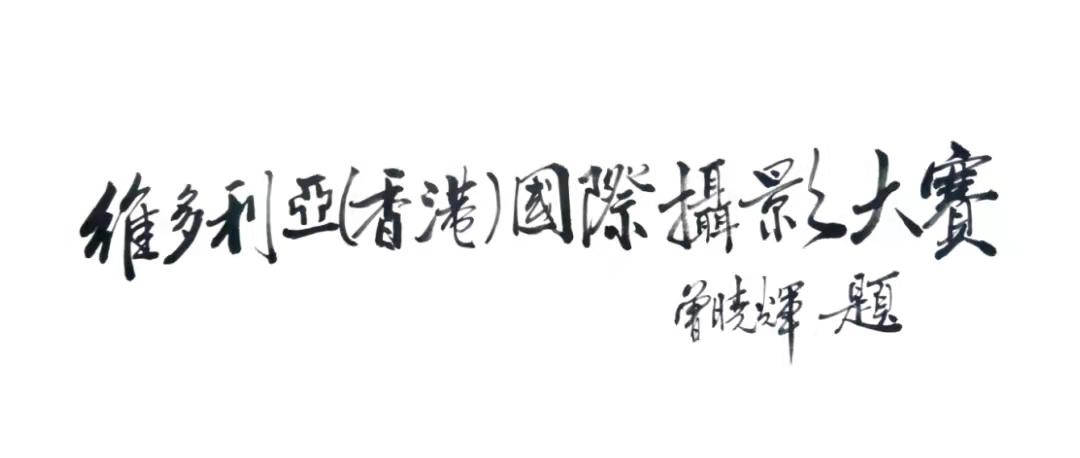故乡!看来我真回不去了
原创、杨晓峰
我开着车子顺着平坦的乡村公路疾驰。道路两边,楼房别墅鳞次栉比,大多数门前都停放一、两辆轿车或货车。屋子里笑语喧哗,穿着光鲜的男女老幼进进出出。乘着回乡过年的机会,大伙都在走亲戚、“往年酒”。二哥一边看着回乡窗外的景致,一边兴奋地与母亲交谈感受。他到兰州务工10多年,今年第一次回金川区西坡村过年,但老家房子破败住不得人,只好留在城里,与母亲兄弟一起过年。这次到乡下姑姑家,就是他的提议,父母极力赞成,我也想了却一桩心病,几人一拍即合。
我们都是把姑姑家当成还能回得去的故乡了。
姑姑家住在宁远堡镇西坡村。宁远堡镇也是百年古镇,然故乡偏偏“金头银身子,屁股夹着黑尾把”,山称“龙首山”,水往坑流。我的老家在龙首山金川区西北角的西坡村,水来成灾,水去成滩,小时常常到姑姑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有年竟住两月之久。姑姑家诗书传家,忠厚继世,家境殷实,长子如祥大我几岁,在姑姑家的日子就成了我们的嘉年华。我们钓鱼、采野菜、掏鸟蛋,凡是童年能干的坏事、好事几乎全干了遍。
看见姑姑家院子的时候,车子停下靠在路边,我们踏上一段蜿蜒的麦田埂。姑姑家人见车来,早指使小孙子接到田埂中央。我把手中包裹让给孩子,一溜小跑,先进了村落。说是村落,也不贴切,姑姑家与邻居现在都搬住在西坡村重新盖的楼房,一排一排,煞是现代气派,只是没了过去村落的气象。门口遇姑姑,拉住我手,满面欢喜,左看右看,亲热得不行。携手进屋,姑姑佝偻着腰,笑容可掬,却略显僵硬。姑姑把我拉到板凳上坐下,又趔趄着去门外接母亲。姑姑回来说,知道我们要来,天一亮就起了床,不料一激动犯了病,十分疼痛,出不得门。我这才注意到,姑姑躬着腰,腰间系了根皮带,皮带陷进棉袄里,几乎看不见。我的内心涌起一阵内疚,劝她进里屋歇息。她却不肯,强撑着陪我。我一下子兴趣索然,与姑姑的聊天就有些心猿意马。趁着母亲与婊嫂相互搀扶着进门,溜将出来,发现二哥与表哥等在门口摆了茶水摊,聊得正欢。
表哥与二哥一样,长年在外务工,年前才带家眷回乡过年。大伙坐到一起,免不得勾起往事,相互打趣,过去谁的鬼怪故事讲得好,谁的歌唱得好,谁与谁摔跤老输,谁偷过谁家的白菜,谁在念初中时跟女同学眉来眼去,等等。
我也插不上话,我突然想起一事,说,印象中姑家院子里有二株树,一株老枣树,还有一株葡萄树。白杨树长在北面沟边,树干粗壮,树冠里藏着喜鹊窝,每天“唧唧喳喳”不停,我们拿着弹弓射击,可因人太小,力太弱,根本射不着。那时的喜鹊不怕人,甚至懒得看我们一眼,立在枝头照样鸣啭;老枣树生在姑家的房院里边,枝叶茂盛,弯着树干,地上凸起嶙峋的根蔓,生出许多小枣树,每年秋季老树硕果累累,竹竿够不着,摇也摇不动,我们就抛砖瓦打枣。有时枣没打到,自己额头却落个包,但并没人喊痛;葡萄树就在姑家花池里,拖着长藤扎成一绺,挂在几株临水而立的老柳树上。葡萄成熟时,过往的人伸手随意采上一串,尝个新鲜。有时暑假结束葡萄还没红,我却要从姑姑家赶回去上学,就把青葡萄采上几串,揣进书包里带回。课堂上打瞌睡,摸出一颗扔进嘴巴,酸在嘴里,美在心里,赢得同学们几多艳羡!
来时路上瞭望,这几株树好像没了?我问。
表哥答,早没了。
我把姑姑家当成还能回得去的故乡,故乡于我,看来真将回不去了
原来,这些年人们外出务工经商,西坡成了“空心村”,只有几位老人独守空巢。后来,外出的人挣了钱回乡盖房,嫌村里局促,就在村外另择地方。随着“空巢”老人逐一离世,活着的也搬入了外村的新居,老村子没了“人气”,房屋年久失修,渐次倒塌。白杨树的户主是个“五保户”,去世后树没了主,被人砍了换了钞票;枣树是在村子里无人住后,有人在空地上种庄稼,怕枣树遮荫,索性砍伐了去;葡萄树是在柳树全蛀倒后,藤子趴在了沟里,被淹死了。
几株树的命运始料未及,我的心头一阵掏空般难受。趁他们不注意,起身独自转到楼后村子的沟坝地。沟坝已颓坍成一道土埂,泥泞不堪,勉强可以行人;水沟严重淤积,沟水只有脚踝深,沟底显现厚厚一层褐色的树叶——我就是在这学会游泳扎“猛子”的呢!水沟东拐角水中央那座小湖,记忆中长满草树,密不透风,是鸟的“天堂”;现在上面仍有树草,但枯黄孱弱,稀疏寂寥。欠着脚走进村子,满眼残垣断壁,破败衰落。稍平整的地方种上了小麦,麦苗稀稀拉拉,杂草丛生,看得出主人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管理粗放,任由其自生自灭。其实不光是村子里,就是正儿八经的田地,现在种庄稼不都管种管收不管理吗?!
开饭了。姑父到底敌不过病疼,进屋躺下了,没有上席。一桌的美食,却唤不起童年味美的记忆。席间,母亲和二哥给表哥当说客,劝姑说,老俩口都年近九旬,一旦有个大病小灾,谁来照应?还是随孩子一起到外面生活吧。姑叹口气,嗫嚅着,不服老还真不行,看来也只有这样了……
我一旁听了,默默地想:姑父姑妈随表哥走了,我还到哪去寻这么一处心灵的港湾?
故乡!看来我真的回不去了!
 会员投稿
会员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