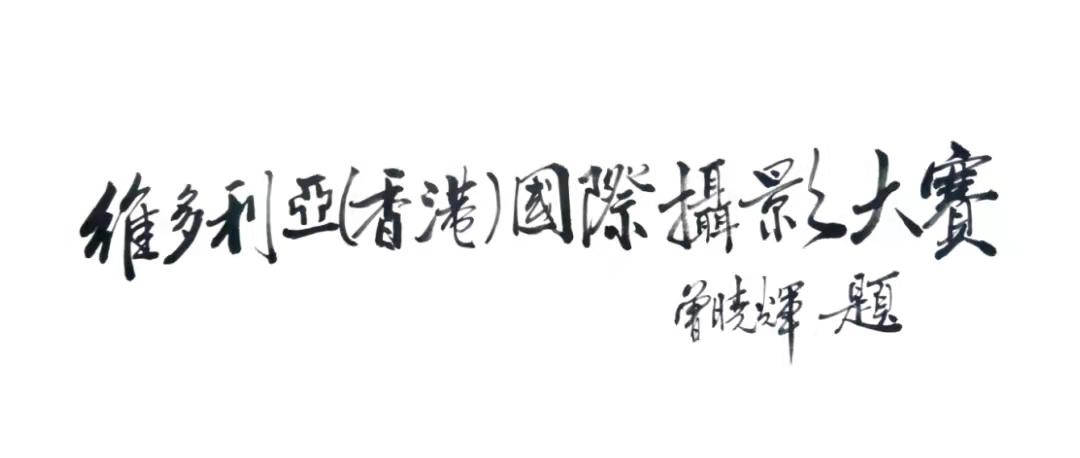雪,终于还是来了,心,也就放松了下来,好似下了雪,放了鞭,就算是过了年。不过再也没有兴奋的劲,但绝不是不高兴,只是已经习惯而已。
那雪,本就是不期而遇的,天气预报员早早地说是多云,她偏要不服管教调戏一番。洋洋洒洒,飘飘荡荡,竟然是越下越大,战斗了一整个白天。
天灰蒙蒙的,再没有往日的幽蓝,湮没了西边雄壮的太行山脉。路光滑滑的,再没有从前的坚实,抛光了脚下宽阔的光明大道。小孩子倒是高兴的很,一蹦一跳,欢跳雀跃,不怕冷,也不怕滑。树缩成一团,萎缩着不让这天上来客亲近。冬青就不行了,被她盖住了头,旁边的垃圾桶好似戴了个纯白的帽子,休息的车车也被厚厚的围上了,就连紧挨着的长椅也像是垫上了厚厚的棉垫子,一片落叶寂寞的坐在上面,不知是不是想到了遥远的故乡。
故乡,今天没有雪。
故乡若有雪,定是像巴金先生说的“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然后就能像鲁迅先生看见的那样塑罗汉,当然也可以像闰土那样捉麻雀,山尖照理是“给蓝天镶上了一道银边”,哪怕是“和影子瑟瑟立在雪中”,也是会“令人想到美丽的春天”。
可是,这些都还不重要,重要的是母亲的喜悦。这个时候,她看着院子里渐渐增厚的雪,总是会微笑着说:“大雪兆丰年啊!”
是啊,麦子的收成永远是她最最关心的。雪啊,你飘到故乡可好?
 会员投稿
会员投稿